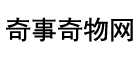杨泉在认真研究天文、地理、工艺、农学和医学的基础上,写下了《物理论》等重要著作,两汉以来自然观;并从庶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以主义自然观为武器,对门阀士族的御用思想武器—玄学进行激烈的批判。
杨泉反对玄学的斗争是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一个侧面。
研究杨泉的主义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对于了解今天自然科学战线上的现实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斗争的重大问题承认天变,还是天不变,这是当时玄学与反玄学斗争的又一重大问题。
由于儒家一度已被搞臭,玄学家不敢直接搬用汉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而是采取比较隐晦曲折的形式,继续散布“天道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
他们表面上承认万物的运动变化,但实质上仍以绝对不变的“寂然至无”当作万物之本。
在他们看来,运动是相对的,静止是绝对的。
功只是静的表现形态。
尽管万物变化无穷,但决定万物变化的“虚无”之“道”,却是永远寂然不变的。
“天地虽人,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王弼:《周易注二复卦》)玄学家以虚静为观察世界的总观点,设计了一个“静—动—静”的玄学公式:“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
”(王弼。
《老子注》第十六章)这里很明显,运动是从不功的虚无中产生的,出发点是“虚静”,归绪点又是“虚静”玄学家的形而上学观点可谓彻头彻尾。
杨泉根本反对玄学家的动静观,认为自然界上白天体,下至地上的万物都处于不停的运动中。
他说:“天者,旋也,均也。
积阳为刚,其体铡旋,群生之大仰。
”天体犹如一个大的旋转器不停地运动着。
产生运动的原因,不是来自神秘的外力,也不是山于“虚静”的“无”,而是取决于自然界对立的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
“惟阴阳之产物,气陶化而播流。
”(《蚕赋》)不论是“喜风”、“怒风”、“清风”或“固风”,也不论是东北风、东南风、西南风或西北风,只要是风都是“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
这是“自然之理”,“非有使之者也”,并投有什么造物主在幕后操纵。
他还认为昼夜的长短变化也是由于阴阳二气制约的结果。
“夏则阳盛阴衰,故昼长夜短;冬则阴盛阳衰,故昼短夜长,气之引也。
”这样解释虽不确切,但他能从自然界本身的矛盾性来说明自然现象,并得出阴阳二气的扣互作用是“天下之性,白然之理”的结论,初步接触到阴阳二气的矛盾是万物的本性和普遍规律的问题,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是位得重视的。
此外,杨泉还注意到一些自然现象的相互联系,指出“潮有大小,月有盈亏”,认为潮汐大小与月亮盈亏有着一定的关系。
他并不懂得这一相互关系的真实原因,但他能从“月,水之精”这种朴素的思想来解释这一关系,这也是很难得的。
人定胜天轻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人民,反对“人定胜天”,是一切主义者共同的特征。
玄学家承袭孔孟之道,极力散布“顺吉逆凶,天之命也”(王弼:《论语注·季氏》)的夭命观,宣扬“自然无为”的听天由命的思想,反对参加生产实践,反对改造自然。
他们胡说什么“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
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一也。
方(王弼:《老子注》第廿九章)认为人们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而不能积极地去“造为之”,否则,就必定失败,极力鼓吹消极无为的悲观论调。
他们还散布“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的主义先验论,胡说“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也。
分(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七章)在他们的心目中,亲身实践的劳动人民最无知、最卑贱,只有他们这些贵族老爷才是高贵有知的。
他们吹捧孔老二是圣人,吹嘘“儒雅博道,莫贤乎董仲舒”,(何晏;《冀州注》)宣扬“贤愚有别,尊卑有序”,“上守其尊,下守其卑”(王弼:《周易注·鼎卦、泰卦》)的尊卑等级思想。
他们出于内心的恐惧,扬言“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王弼:《老一子注》第五十七章)害怕劳动人民一旦觉悟就起来造反,因而极力推行“令无知无欲”,“使其无心于为也”的愚民政策。
这种毒辣的手段,充分暴露出玄学家宣扬“自然无为”的本质。
与玄学家相反,杨泉反对玄学的“白然无为”,肯定法家的“人定胜天”,并突破尊卑等级观念和“上智下愚”的思想,在与劳动人民的接触中,对农业生产和劳动人民的技能和智慧给予重视和赞扬。
正当玄学家大乱“玄风”、轻视技艺的时候,杨泉却在《织机赋》中,赞扬“伊百工之为技,莫机巧之最长”,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纺织工人勤劳灵巧的优美形象。
他在《物理论》中写道:“夫工匠经涉河海,为加艘以浮大渊,皆成乎手,出乎圣意。
”称赞造船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的双手,.称赞他们造出大船航行于大海的丰功伟绩,点出工人“经涉河海”的实践出智慧、出成果的真理。
他还特别强调人优越于动物的根本点在于“出乎心,巧成于手”,能够制造有用的器具。
他说:“夫蜘蛛之罗网,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况于人乎!故工匠之方圆规矩出乎心,巧成于手。
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勋形成器用哉?”没有工人的智慧和双手,那里能制造精致的器具,建立显著的功勋呢了在当时那种谈玄说虚、不务实际、轻视劳动人民的社会里,杨泉如此颂扬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活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杨泉对农业生产也颇关心。
这是和当时法家实行的农耕政策分不开的。
他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提出稼和稿、种和收的关系问题,指出“种作日稼,稼犹种也;收敛日稿,楷犹收也。
古今之言云耳。
稼,农之本;墙,农之末。
本轻而末重,前缓而后急。
稼欲熟,收欲速,此良农之务也。
”(《物理论》,见《齐民要术·种谷第只》)这就是说,耕种是农业生产的起点,收获是农业生产的结果。
耕种轻率迟,收获就紧急而繁重,因此耕作要熟练,收获要迅速,这是搞好农业生产的基本任务。
他还具体分析了种子的差异和土质的不同,对于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指出“凡种有强弱,土有高柔。
仁宜强,高茎而疏粟,长稼而粒大。
”这是在朴素思想的支瓦下,对劳动人民耕作经验的总结。
结语总的来说,杨泉的主义观自然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他没有被滚滚的“玄风”所刮倒,而是勇敢地拿起自然观这个武器,针对玄学展开尖锐的批判,在当时的思想领域里树起一面反玄学的旗帜,对尔后的思想家、科学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北魏具有法家思想的农业科学家贾思拐,曾在他的巨著《齐民要术》中,不止一次地引用杨泉《钧理论》关于耕种、养蚕等论述。
南北朝无神论者何承天、范填等,也与杨泉的无神论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杨泉,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彻底批判玄学。
他的自然观是素朴的,不彻底的;他在探讨天体运行时,坚持了见解,但又保留“言天者必拟人”的思辨方法,混淆了天体与人体的本质差别;他论述了精神对于形体的比较关系,但对于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则缺乏明确的观点。
他的薪与火的比喻包含有把精神看作物质的错误;他充分肯定劳动人民的聪明才能,但又过分强调“贤人”、“清忠之士”的作用,仍然没有摆脱英雄史观的羁绊。
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杨泉仍不失为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朴素主义者。
从杨泉的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自然观上的玄学与反玄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