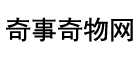光业寺碑左侧拓片(局部)
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论隋唐两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和“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颠覆性论断在唐史学界几乎无人不晓。陈寅恪据以作出这一判断的关键性资料是当时“河北省隆平县”尚存的光业寺碑文。《光业寺碑》记载了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李熙建初陵、第三代祖李天赐启运陵在当时赵郡象城县(后称昭庆县,即民国时期的隆平县、今天的河北省隆尧县)营建、祭祀以及在陵侧兴建光业寺的情况,特别是其中“维王桑梓,本际城池”等语,明确反映了当时的象城县为李唐先世“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之地”,从而为陈寅恪解决李唐先世究竟是陇西李还是赵郡李的历史公案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其实,这只是该碑史料价值的一个方面,即通常人们所知的碑阳所镌刻的文字,实际上该碑还有另外一个极少为人所知、却丝毫不逊色于正面政治史资料的价值,即镌刻于碑阴碑侧的大量有关唐代村落和唐人姓名的题记文字,对唐代村落史和社会史具有极其重要的独特价值。
反映唐代村落和唐人姓名的石碑石刻并不鲜见,但光业寺碑碑阴碑侧题记文字量和内容都值得关注。光业寺碑属于体量极大的唐碑。据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第4期)一文介绍,光业寺碑碑身碑首现高4.37米,其中碑身高3.02米、宽1.4米,厚度为31.5厘米。这一体量与现存全国体量最大的唐代何进滔德政碑(现存大名石刻博物馆)相比虽稍逊一筹,但在现存唐碑中仍堪称佼佼者。该碑的碑阳为正文,题记则密密麻麻分布于碑阴和两面碑侧以及四角磨平的斜面。据笔者现场观察,题记文字除了任县等官员以及捐资组织者都维那等姓名为大字外,其余都是字径2.5厘米左右的小字。其中碑阴及右后角、左后角斜面文字有40行,碑左侧及左前角斜面文字有12行,碑右侧及右前角斜面文字共有13行,全碑题记总共65行,总数在5000字以上应无疑义,其中可以释读的文字达3970个以上。该碑作为附属文字的题记量相对于作为主体文字的正文字数所占比例极高。光业寺碑正文文字数量李文做过统计,经过补缀之后,“共得碑文2904字,尚缺55字”。而题记文字量超过正文文字量近50%。我们知道,唐碑碑阴多有题记,字数动辄成百上千,但以官员题名题衔居多。反映基层社会的造像碑、经幢题记虽然也有不少普通民众的题名,但涉及村名的很少。所以,像光业寺碑这样巨量篇幅、极高比例集中刊载大量村名与众多村民题名的唐碑确实少见。
光业寺碑题记具有村落史、社会史、民俗史和地名学、姓氏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仅从村落史的角度看,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第一,反映了唐祖陵周围两州三县交界地区的农村社区体系。题记现在保留的村名,李兰珂《李唐祖籍在隆尧》一书称有40多个,但列出的村名只有35个,笔者根据现场观摩和拓片录文查核,除已列村名之外,题记中还可见到□鲜村(“鲜”前一字不清,不排除该村即名“鲜村”的可能)、八王村、张李村、南杜村、南霍村、□霍村和郝村等,加起来确有40余村,如果将已经残泐约四分之一的碑面包括进来,按比例计算原来村名至少应有50余个。根据碑阳正文,参与营建、集资和祭祀的官民僧俗包括赵州象城和邢州柏仁、任县“两州三县”的“得姓同封或里仁从宦”。这50多个村庄应该就是以唐祖陵为中心募集唐祖陵、光业寺佛堂和碑刻营建修缮资金而形成的农村社区体系,是一个跨越州县两级行政区而在三县交界地区形成的特殊社区体系,为我们了解唐代跨行政区的农村社区体系开展集资、营建等活动提供了典型的实证资料。
第二,反映了唐代前期村落格局单一制为主的典型结构。我国村落名称中,称“村”“庄”者为多数,光业寺碑题记出现的村名全部称“村”,反映了唐代前期村落名称亦即村落格局单一制为主的特点。光业寺碑建于开元十三年(725年),这个时代节点很重要。关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陈寅恪有精辟的论断,称“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二期,而以玄宗时安史之乱为其分界线”,“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其实,唐代村庄结构同样有前后期之分,以唐玄宗时期作为前后期的分界点也同样适用。我们知道,唐代村落的基本形式或者说主要形式是“村”。村作为一种自然聚落自东汉时期产生之后,在南北朝时期获得很大发展,至唐初才被纳入行政体系。《旧唐书》卷48《食货上》称:“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中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伍家为保。在城邑居者为坊,田野者为村。”《通典》卷3《食货·乡党》引唐令称:“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可见唐代的“村”类似现在的行政村,是乡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