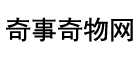朋友之间可喻为雨中的伞、指路的灯。双方心理契合更为深度时,可称之为知己。接下来小编分享两篇著友情的故事吧。
55年的友谊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9。0级大地震。这之后的几天时间里,76岁的广州老伯蔡风(化名)一直在收看电视里关于日本地震的最新灾情报道,同时寻找着自己的日本笔友——72岁的佐藤喜子。
55年前,一封自中国辗转寄往日本的信件,使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他们曾在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年代里失去联系37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蔡风十分揪心,好不容易在16年前恢复联系的两个古稀老人,是否会因为地震,从此天人两隔?
55年的友谊佐藤喜子,你在哪里
3月11日下午,蔡风终于下决心要打一个电话。这是一个国际长途,电话那头是住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泉区的佐藤喜子。
蔡风不会日语,也没去过日本,佐藤喜子不会中文,也没来过中国。两人不但没见过面,连电话都没有通过。他们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是几封跨越55年的书信。
这是蔡风打给佐藤喜子的第一个电话。“老朋友,您可千万别出事啊。”看着电视里日本正在经历的浩劫——9。0级的地震及其引发的破坏力惊人的海啸,蔡风有点儿坐不住了。
苦于自己不会讲日语,蔡风当天下午就找到了广州樱花日语学校校长马燕。马燕当即拨打了佐藤喜子家的电话,但电话无法接通。
没有人相信蔡风有一位好朋友在日本,而且两人通过书信交往超过了半个世纪。
“我保存着她寄给我的所有信件,信件中我们叙述彼此的人生,无话不谈,从年轻一直说到一头白发。”蔡风说。他打开一本很大的相册,里面夹着一沓发黄的信件。
最早一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956年11月25日,当时的佐藤喜子还是日本一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正为能和蔡风结为笔友而心怀喜悦。
最近一封来信的落款日期是2011年1月11日,72岁的佐藤喜子已白发苍苍,抱上了孙子。
这些信件全部用日文书写,为了方便阅读,蔡风请人帮他翻译成中文。同样,佐藤喜子每次也要找人将蔡风用中文写的书信翻译成日文。
蔡风的相册里还保存着佐藤喜子50多年里寄来的数张照片和一些日本邮票。“她哥哥喜欢集邮,这些邮票都是她1957年寄给我的,现在非常珍贵。”看着这些邮票和照片,蔡风的情绪极其低落。房间的电视里还在不断更新日本地震的遇难者人数,仙台市的一些沿海小镇里大水压境,汽车成了海水中的一叶扁舟,被冲得翻了过去……
异域洞天
1956年,21岁的蔡风在广东北部山区的韶关气象站工作。山区生活单调,蔡风只有通过读报获取信息。1956年年中,他看到《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日本女青年早濑笙子希望与中国青年互通书信的消息。
蔡风瞒着身边所有人,悄悄给早濑笙子写了一封信,寄往《中国青年报》,该信随即被转到了日本。
由于中国青年寄给早濑笙子的信太多,在发动家人回信仍无法应付的情况下,早濑笙子把蔡风的信转给了在福岛县川俣高等学校读大二的女学生铃木喜子。
1956年11月25日,铃木喜子在日本的冬天里,给蔡风写下了第一封信。
收到信后,蔡风看不懂日文,只好将信寄给《中国青年报》请求翻译。很快他就收到了译在中国电影出版社稿纸上的信件。
在这封译成中文后仍有1000多字的长信里,铃木喜子说:“今后我很希望作为您的一个通信笔友一直和您通信,请您做我的朋友吧。”她还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生活环境。
铃木喜子说,她每天早上7点半坐13分钟的火车去上学,说日本就要下雪了,冬天就是围着火炉看看书,或是打打羽毛球,有时也踢毽子。她说自己所在的福岛县饭野町是个小镇,家就在火车站旁边,“到村庄的任何地方去,都用不了10分钟。”
她说饭野町唯一有风景看的是一个堤坝,“春天好多人来这里看樱花和梅花,夏天有很多人来游泳,我也是其中一个。枫叶变红的季节,这里是很美丽的,过了这个季节就和普通的村庄一样了。”
铃木喜子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服装,尤其是对刺绣的喜爱。她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甚至问蔡风每天穿什么衣服工作。她说自己工作时会在上衣和裤子外边套上围裙。
“请保重身体,以后天气会冷下去的。”铃木喜子这样跟蔡风说。
在信中,铃木喜子附上了一张夏天里自己在福岛县苗代湖边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17岁姑娘身穿长裙,低眉浅笑。
隔海相望
1957年2月20日,铃木喜子给蔡风写来了第二封信。
此时的铃木喜子即将毕业,在东京游玩。她在信中倾诉了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已经不胜渴望还乡,每天都有思乡的病。”
铃木喜子在信中表达了对就业和未来的担忧。她说日本土地狭窄,而且人口众多,就业是件艰难的事。铃木喜子动容地对蔡风说:“你能为着我,而在别国的天地间守望着我吗?请求你。”
1957年,蔡风到北京出差的时候,拿到了铃木喜子托人带到北京的49张邮票。这些跨越中国清朝、伪满洲国、军阀混战等历史时期的珍贵邮票,至今被蔡风收藏着。
从这封文末署名为“从别国的友人寄给隔海的彼岸友人”的信之后,蔡风和铃木喜子就失去了联系,隔海相望,一晃就是37年。
1958年,蔡风被派往西沙群岛进行气象勘测,一去就是3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大跃进”,蔡风回到广东后,又赶上了3年自然灾害,再往后是长达10年的“”。中日关系在其中沉沉浮浮。
失去联系的37年里,蔡风与喜子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一步步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头发斑白的老人。
1963年,在3年自然灾害的尾巴上,蔡风经战友介绍,认识了广州一家染织厂附属幼儿园的一位女老师,两人随即结婚。对于蔡风与铃木喜子互通书信的事,蔡风的妻子刚结婚时就知道了。回到广州后,蔡风进入广东省气象局工作,直到退休。
1962年,在隔海相望的另一端,23岁的铃木喜子先于蔡风一步,与日本国铁公司的员工佐藤兴源结婚,自此随夫姓,改名佐藤喜子。
心念故人
1994年,与喜子中断联系37年后,当年风华正茂的蔡风已经59岁。一次他在翻检旧物时,看到喜子在1957年托人带给他的邮票。蔡风用心地将邮票寄往昆明,找了一个熟悉邮票的朋友鉴定,得知邮票经过数十年收藏,价值不菲。他再度想起异国的这个笔友,试着按照喜子当年的通信地址,又写了一封寄往日本的信。
“写这封信的时候,真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达你的手中。因为离开我们曾经互相通信的时间——1957年11月,已经将近40年了,真是岁月如梭啊。当年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则差不多是老人了……但是你寄来的信、照片和礼物,我一直珍藏到现在。不知你是不是还记得远在中国这个曾经的通信笔友呢?”蔡风不知道老朋友已经更名为佐藤喜子,他依然按原来的称呼给铃木喜子写信。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喜子一家已经从福岛县饭野町搬到了宫城县仙台市,但是这封信还是通过喜子的妹妹,转到了她手上。
1995年5月31日,佐藤喜子给蔡风写了回信。信中说,对于接到一个失去联系近40年的老朋友的来信,她感到很吃惊。此时的佐藤喜子刚刚退休,但是身体不好,每天要去医院做理疗。退休后的她,最大的兴趣是园艺,在自己家小小的庭院里种着蔷薇和四季开放的花儿。
“时间过得真快,再提笔已过了40年,年少的时光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眼前。”佐藤喜子在信中感慨道。最后,佐藤喜子还与蔡风互勉:以后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幸福地生活。
自从1994年重新建立联系后,此后每年,蔡风都会与佐藤喜子互通书信。每年春节前后,两位老人还会互寄贺卡,祝愿对方全家健康。
他们也互相留下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但两人依旧像当初一样,只是保持书信联系。语言的障碍在两人中始终存在。“主要是我们都不懂对方的语言,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蔡风说。
生死惦念
这次地震,第一次打破了两人50多年来的交流方式。蔡风几乎是第一时间看到了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他很担心佐藤喜子一家的安危,于是拿起电话,想知道另一头的日本老朋友是否安全。
3月16日,久等之下还没有佐藤喜子的消息,蔡风想到了求助媒体。在广州一家都市报的帮助下,记者将寻找佐藤喜子的消息转达给了读卖新闻社、朝日新闻社和国际红十字会等媒体及机构。但是仙台已成地震重灾区,各组织均表示找人难度很大。蔡风寻找失散笔友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一些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以及日本网友也加入到寻找佐藤喜子的队伍中。
大灾之下,蔡风对相交55年,仅凭书信交往的佐藤喜子的担忧和寻找,令所有人动容。
76岁的蔡风还用起了电脑,查看日本的电子地图。当发现佐藤喜子家所在的仙台市泉区,位于仙台市西北方向,地势较高后,他坚信佐藤喜子一家会平安无恙。
3月18日晚6时10分许,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日本传来。几经辗转,佐藤喜子与记者通上了电话,她说:“我没事,全家人都很好,感谢中国朋友的关心。”
电话里,佐藤喜子表示,这次地震和海啸对宫城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是幸好她家所在的仙台市泉区不在海边,因此没有受到海啸的影响。她的丈夫佐藤兴源地震时正好在印度尼西亚,家里其他人地震后一直待在家中。
谈起灾后生活,佐藤喜子说已经可以去商店里买一些食物了。经过连续抢修,目前她家所在区域供水供电已经恢复,可以洗澡了,不过煤气还没有恢复。
得知蔡风在四处求助打听她的消息时,佐藤喜子深受感动,她再三请记者帮忙转达,要蔡先生不要担心,过段时间她就会写信给蔡风。
佐藤喜子称赞蔡风,说:“他真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很好的人,一直很关心我和家人的生活。请代我转达:我现在安好,谢谢他对我的关心!特别是地震后那么关心我和家人的安危,真是非常感激!”
得知佐藤喜子一家平安,蔡风连声说:“非常高兴,太高兴了。也希望佐藤喜子他们从灾难中走出来,重新安排生活。”
他说自己也很期待着佐藤喜子接下来的来信,更期待着双方能见一次面,完成毕生的夙愿。
缺少你,纽约变得平庸
一天天黑后,我开着车拉着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段时间,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在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开着车到处乱窜。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怕。
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识路,所以老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
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是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一踩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刹住车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
缺少你,纽约变得平庸那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我一下子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北京人,大学读了不到两年,觉得没劲,毅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纽约待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他喜欢搞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他会把篮球装进编织袋中,从楼顶抛下。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一年圣诞节的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那人刚坐下,就被他从后面用塑料袋套上脑袋,憋得满脸通红。艾未未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式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他,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说他车上价值200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艾未未听后,出去转了一圈,他只花十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一台音响送给李争争。李争争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台!”
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盲目地东游西逛。艾未未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一脸坏笑地补充:“可以给你留下一幢。”他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简单。他曾经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座房子,保证花钱不多,又非常牛。”他说,“你买四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听了。热血沸腾,到处打听买一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
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个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异口同声地说:“牛。”这—座房子,—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
现在,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你们太落后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很简约,非常水泥了。”
只要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艾未未。有他在纽约,那里就是—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年以后,我再次回到纽约,发现缺少他的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