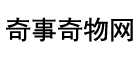“笑不露齿”的上一句和下一句是什么?
笑不露齿的出处出处:《女论语》:“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笑不露齿这句话知名度很高,一般是用来形容女子的美德的,这句话出自大唐时期清河的女子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写的《女论语》:“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语莫掀唇意思就是笑不露齿,封建社会女子所尊从的教训象笑不露齿、行不摆裙、三从四德等许多都出自《女论语》,在古代,这些是女子应该学习的道德。在现代,这些成了封建余孽。宋若莘在唐朝是有名的才女,被封为女学士。 古代笑不露齿的第一人 《女论语》--唐代 宋若莘、宋若昭著 宋若莘---(?--820年)贝州清河(今邢台清河县)人,父廷棻,生一男五女,男独愚不可教,而五女皆警慧,善属文。若莘最长,次为若昭、若伦、若宪、若荀,皆禀性贞素,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若莘诲诸妹若严师。贞元中,李抱真表其才,并召入宫。帝与侍臣赓和,五人咸预。高其风操,不以妾侍命之,呼为学士。若伦、若荀先卒。贞元七年,(公元七九一年)诏若莘总领秘阁图籍。卒,赠内河郡君。若莘著有〈女论语〉十篇,妹若昭又为传申释之,传于世。
请问:“笑不露齿,行不摆裙”出自于哪本书?
应当出自《女四书》中的《女论语》
《女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四种女子教材——《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的总称。《女四书》中所汇辑的上述四本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进行女子教育的专书,旨在阐发儒家所宣扬的“三从”、“四德”的妇道,培养封建思想品格的“贤妻良母”。
女子教育是中国古代整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经籍中就有关于女教的思想。如《周礼·天官·冢宰下》:“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里提出女教的“四德”。《仪礼·丧服·子夏传》提出了妇女无专制之道,而有“三从”之义,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易·恒》中“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诗·大雅·瞻印》宣称:“妇无公事”,等等。这一切说明中国早在封建社会之初,封建统治者就注意并且实施女子教育,但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教科书。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特别自汉代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统治者为了加强其父系宗法制的封建专制秩序,就日益注重和大力倡行儒家礼教及女子教育主张,要求妇女明达诗书与坚守‘妇礼”而能“齐家”,从而有助于封建王朝的治国及维持其统治秩序。在这种形势和要求下,开始出现了女子教育专著,这就是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昭写出的《女诫》。自此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陆续编撰出一系列的女子教育的单行课本。迄明朝晚年,从历代 的女子教材中选取出上述的四本书,汇编成为成套的《女四书》。
林语堂写过《女论语》一书吗,如果写过,怎么网络上搜不到,还是该书有其他名称,或者还是只是一篇文章?
这是原文
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
“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
“What a strange thing is man! and what is stranger is woman!”
请不要误会我是女性憎恶者,如尼采与叔本华。我也不同意莎士比亚绅士式的对于女人的至高的概念说:“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我喜欢女人,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用不着神魂颠倒,也用不着满腹辛酸。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男人一生抽烟、田猎、发明、编曲,女子却能养育儿女,这不是一种可以轻蔑的事。
我不相信假定世上单有父亲,也可一看管他的儿女,假定世上没有母亲,一切的婴孩必于三岁以下一起发疹死尽,即使不死,也必未满十岁而成为扒手。小学生上学也必迟到,大人们办公也未必会照时侯。手帕必积几月而不洗,洋伞必时时遗失,公共汽车也不能按时开行。没有婚丧喜庆,尤其一定没有理发店。是的,人生之大事,生老病死,处处都是靠女人去应付安排,而不是男人。种族之延绵,风俗之造成,民族之团结,都是端赖女人。没有女子的社会,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世上没有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有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男人不会居住在漂亮的千扁一律的公寓、弄堂,而必住于三角门窗而有独出心裁的设计之房屋。会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而且最好的外交官也不会知道区别白领带与黑领带之重要。
以上一大篇话,无非用以证明女子之直觉远胜于男人之理论。这一点既明,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女子谈话之所以有意思。其实女子之理论谈话,就是她们之一部。在所谓闲谈里,找不到淡然无味的抽象名词,而是真实的人物,都是会爬会蠕动会娶嫁的东西。比方女子在社会中介绍某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必不介绍他为有机化学教授,而为利哈生上校的舅爷。而且上校死时,她正在纽约病院割盲肠炎,从这一点出发,她可向日本外交家的所谓应注意的“现实”方面发挥--或者哈利生上校曾经跟她一起在根辛顿花园散步,或是由盲肠炎而使她记起“亲爱的老勃郎医生,跟他的长胡子”。
无论谈到什么题目,女子是攫住现实的。她知道何者为充满人生意味的事实,何者为无用的空谈。所以任何一个真的女子会喜欢《碧眼儿日记》ntlemen Prefer Blondes)中的女子,当她游巴黎,走到 Place Vendome 的历史上有名的古碑时,俾要背着那块古碑,而仰观历史有名的名字,如 Coty 与stier (香水店的老招牌),凭她的直觉,以 Vendome与Coty相比,自会明白Coty 是充满人生意义的,而有机化学则不是。人生是由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而造成的。自然,世上也有 Madame Curie Emma Goldmans 与 Beatrice Webbs 之一类学者,但是我是讲普通的一般女人。让我来举个例:
“X 是大诗人”,我有一回在火车上与一个女客对谈。“他很能欣赏音乐,他的文字极其优美自然。”我说。
“你是不是说W?他的太太是抽鸦片烟的。”
“是的,他自己也不时抽。但是我是在讲他的文字。”
“她带他抽上的。我想她害了他一生。”
“假使你的厨子有了外遇,你便觉得他的点心失了味道吗?”
“呵,那个不同。”
“不是正一样吗?”
“我觉得不同。”
“感觉”是女人的最高法院,当女人将是非诉于她的“感觉”之前时,明理人就当见机而退。
一位美国女人曾出了一个“美妙的主意”,认为男人把世界统治得一塌糊涂,所以此后应把统治世界之权交与女人。
现在,以一个男人的资格来讲,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我懒于再去统治世界,如果还有人盲目的乐于去做这件事情,我是甚愿退让,我要去休假。我是完全失败了,我不要再去统治世界了。我想所有脑筋清楚的男人,一定都有同感。如果塔斯马尼亚岛(在澳洲之南)的土人喜欢来统治世界,我是甘愿把这件事情让给他们,不过我想他们是不喜欢的。
我觉得头戴王冠的人,都是寝不安席的。我认为男人们都有这种感觉。据说我们男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也是世界命运的主宰,还有我们男人是自己灵魂的执掌者,也是世界灵魂的执掌者,比如政治家、政客、市长、审判官、戏院经理、糖果店主人,以及其他的职位,全为男人所据有。实则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去作这种事。情形比这还要简单,如哥伦比亚大学心理教授言,男女之间真正的分工合怍,是男人只去赚钱,女人只去用钱。我真愿意看见女人勤劳工作于船厂,公事房中,会议席上,同时我们男人却穿着下午的轻俏绿衣,出去作纸牌之戏,等着我们的亲爱的公毕回家,带我们去看电影。这就是我所谓美妙的主意。
但是除去这种自私的理由外,我们实在应当自以为耻。要是女人统治世界,结果也不会比男人弄得更糟。所以如果女人说,“也应当让我们女人去试一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出之以诚,承认自己的失败,让她们来统治世界呢?女人一向是在养育子女,我们男人却去掀动战事,使最优秀的青年们去送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但是这是无法挽救的。我们男人生来就是如此。我们总要打仗,而女人则只是互相撕扯一番,最厉害的也不过是皮破血流而已。如果不流血中毒,这算不了什么伤害。女人只用转动的针即满足,而我们则要用机关枪。有人说只要男人喜欢去听鼓乐队奏乐,我们就不能停止作战。我们是不能抵拒鼓乐队的,假如我们能在家静坐少出,感到下午茶会的乐趣,你想我们还去打仗吗?如果女人统治世界,我们可以向她们说:“你们在统治着世界,如果你们要打仗,请你们自己出去打吧。”那时世界上就不会有机关枪,天下最后也变得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