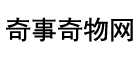鲁迅和秋瑾在日本留学时原本关系极好,为何秋瑾要对鲁迅拔刀?
主要也是因为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众所周知,鲁迅出生在官僚家庭里面,在幼年时期,因为家庭变故,所以他们家族势力早就不如从前那样兴旺了。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就参加了高考,想要做上一官半职,后来他又去了洋学堂念书。在一开始这样的洋学堂受到很多成见,为了救自己,为了救国家,他后来通过考试,远赴日本留学。而秋瑾呢,站在古时女性的性格角度上来看,她无疑是最独特的那个,她喜欢诗词,更喜欢射箭。在古时候女性不能抛头露面的环境下,她总是外出看戏,在许多人的眼中,她的这些行为实属叛逆,而且更让人耻笑。她的家世显赫,最后其父母给她挑选了一个富豪,虽然对方也有着显赫的家世,但文采方面根本比不上秋瑾。秋瑾在嫁人了,因为有娘家撑腰,所以她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到后来她跟丈夫再也无法有共同语言,随后她就去了国外留学,一直到后来鲁迅参加了暗杀组织,再后来被分配了任务的时候,他又临时起了退意,因为他担心家中母亲无人照顾。在知道这件事情后,秋瑾便和鲁迅彻底断绝了关系,再加上后来出现的一些政治事件,他们俩人在意见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最终才拔刀相向。但还有人说秋瑾的这一刀,并非指鲁迅或者具体某人,而是指的这些不愿归国的留学生。
鲁迅和秋瑾曾在日本因为立场不同而有冲突,那在多年之后鲁迅是怎么看待秋瑾的呢
秋瑾和鲁迅,本是老乡,上世纪初几乎同时留学日本。他们两个又都曾写下了以血为题的诗篇。秋瑾的诗是:“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对酒》)鲁迅的诗是:“灵台无计逃神失,风雨如磐喑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秋瑾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理想。鲁迅同样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只是他们革命的方式不同,目的是一致的。
革命成功后,许多人甚至秋瑾昔日的战友,已经将秋瑾淡忘了。但是,曾经被秋瑾“甩刀子”判“死刑”的鲁迅一直没有忘记她。在革命成功六年后,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著名小说《药》就是以秋瑾为原型的。在小说的结尾,荒草离离的坟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国人不曾忘了她。其实,是鲁迅不曾忘了她。
有人说鲁迅刻薄,从这件事来看,鲁迅是豁达的,光明磊落的。他对秋瑾是尊重乃至崇敬的。
鲁迅与秋瑾,是俩个人格伟大的中国人。虽然他们有过过结,但是那不是信仰和原则上的分歧。
秋瑾用她32岁的生命,敲响了一个旧时代的丧钟;鲁迅用他宏大的思想,努力扣开新世纪的大门。他实际在进行着秋瑾未竟的事业。
鲁迅的什么小说中以秋瑾为原型塑造的辛亥革命志士形象?
夏瑜出自鲁迅小说《药》中,其原型是革命英雄“秋瑾”。秋瑾是旧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志士。属激进民主主义派,文中的她为革命洒尽了满腔热忱。而对于她的热血,我们的群众没有让其“白流”做人血馒头,治痨病。治没治好不说,一次与其:疯子的“美名”。
当时的中国在晚清政府的统治夏。一批批的爱国志士,从海外留学归来,一心报国,其用意当然是好的。而凭借他们的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有用吗?他们的勇气是可赞的而每每只得到什么“取义成仁”之类了。但是他们的取义,只使他们的精神成仁,广大的群众并不清楚,并不明白。却反倒气味“疯人”“狂人”。中国封建政府,经几千年而不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此的。
志士先睡醒了,他们颠狂,他们呐喊,他们要为中华民族出力,他们要“医醒”“睡死“的中国人。而最终他们自己却成了“药”沉睡,沉睡,不再沉睡中惊醒就在沉睡中死亡。
而那时的社会却是白睡半醒的。没有是非,黑白的区别。他们只知道喊,而不去教,不去说,是徒劳的。一个民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几个人,可以改变的。只有使他们自己觉悟道才可以。才能革命。
有的人彷徨,有的人呐喊,夏瑜是后者,而他喊醒的是痴人,没有思想,没有大脑,醒后得不道教育,自要兽般的咬其一口。而不知自己被谁叫醒,不知醒来干什么,随大流的苟活着,由于睡着的大无差别了。
夏瑜,为人民而死,为中国而死,是可敬的。死后却得唾骂,又是可悲的。对于革命他清楚,他明白。但他并未读懂人世之情,在可悲之余又是可怜的。为什么不教育他们;不让他们清楚。
“人固有一死,或如鸿毛或如泰山”一座泰山无声得到下,又与一堆烂石的堆砌,有和异呢?
鲁迅和秋瑾在日本留学时原本关系极好,为何秋瑾要对鲁迅拔刀?
鲁迅和秋瑾在日本留学时关系很好,但秋瑾还是因为他的政治地位而对鲁迅动刀,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毕业后,他们去了不同的地方。鲁迅也出生在官僚主义家庭,但他年轻的时候,家庭发生了变化,甚至家庭垮台,父亲也在那时去世。虽然在绍兴,它可以被视为一个面对面的家庭,但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只是徒劳,同时,年轻的鲁迅不能走官路参加科考,也不能进某个官僚的门当助手,于是他走了第三条路,那就是去“外国学校”学习。这所新学校当时没有被中国人接受,很多人认为上这所学校的学生“把灵魂卖给了洋鬼子”,所以他们非常鄙视这类学生,鲁迅要上南京海军学校,学费是8元,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母亲在聚在一起之前,不得不筹钱很久,鲁迅在南京读书时读了很多外国作品,打开视野的鲁迅,看到了这个腐朽破碎的国家,试图思考它的未来和出路,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鲁迅凭借其卓越的成就,获得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会。秋瑾的性格在当时似乎是独一无二的,她写诗,写诗,喝酒,练武术,骑马和弓箭,他甚至出现在公共场合,并去剧院,在当时的人们眼里,他们都是离经叛道的,被人嘲笑的,然而,她并没有认真对待,并给自己取了简虎女夏的名字。萧晓经常与城里的才华横溢的人聚在一起,喝酒、弹钢琴迎战月亮,它有一个名人的风格,不怕过路人的讥笑。然而,由于秋瑾的家世广为人知,向她求婚的富豪官员络绎不绝。最后,她父亲决定选湖南富家子弟王廷军。鲁迅生前说过,他不会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然而,鲁迅从未说过秋瑾的坏话。弃医后,鲁迅在几篇文章中赞扬了她的革命。由此可见,鲁迅虽然不同意秋瑾的主张,但他尊重革命家秋瑾。
鲁迅和秋瑾在日本留学时原本关系极好,为何秋瑾却要对鲁迅拔刀呢?
虽然鲁迅和秋瑾的关系一开始极好,两人是绍兴的老乡,但是鲁迅不是秋瑾心目中的那种爱国青年,甚至对鲁迅的一些做法都是嗤之以鼻的,最后更是起了矛盾,秋瑾直接对鲁迅拔刀相向。当秋瑾来到日本之后,经过同乡会,成为了坚定的爱国主义分子。而鲁迅等人也都是浙江学会的骨干分子,再加上鲁迅曾经多次的集会或者其他的地方发表了慷慨激扬的演讲,激发了很多人的爱国热情。这时的秋瑾对鲁迅的印象是极好的。后来日俄战争即将打响,导致了国内的形势非常的严峻。鲁迅所在的学会认为不光是要宣传知识,还应该有武装起义,为此成立了暗杀组织。而鲁迅后来加入了其中,并且被分配了任务,在任务行动前,鲁迅就说道:“暗杀任务是可以去做,但是假如自己没了,自己的母亲怎么办。”这话就让其他人认为鲁迅退缩了,而秋瑾也知道了这件事,就对他有一些看不起,交往从此也少了很多。后来清政府为了打击这些留学生,就联合日本政府出台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并且引起了轩然大波。秋瑾这时就四处演讲,宣传让留学生回国。而鲁迅却认为不能这样做,因为新规则还没有确认,同时认为自己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回去了也是一事无成,于是主张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从此日本留学生就存在两个分歧,并且日本媒体乘机发表言论嘲笑留学生。陈天华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悲愤跳海自杀。在他的追悼会上,秋瑾为首的人就将鲁迅等不愿回国的人判处“死刑”。并且从靴子里面拿出刀,对准鲁迅。
好像外国的娘儿们牵的哈巴狗一样出自鲁迅哪篇文章
貌似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面提到了这两个关键词,但我好像没读到原句,有兴趣可以自己读一下,很尖锐深刻的一篇文章。
作者鲁迅 一 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②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play)③,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④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⑤。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⑥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⑿。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⒃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⒄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⒅,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⒆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⒇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七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3)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24)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26),《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27)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八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文章注解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②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③“费厄泼赖”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④“义角”即假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⑤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⑥“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⑦康党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指参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⑧“以人血染红顶子”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⑨“咸与维新”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⑩二次革命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⑾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七月十三日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⑿王金发(1882—1915)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于杭州。 ⒀谋主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贪污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杀害王金发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⒁模范的名城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⒂杨荫榆(?—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⒃“犯而不校”这是孔丘弟子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⒅“投石下井”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⒆“请君入瓮”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⒇“党同伐异”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婆理”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22)清流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23)“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24)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25)“求仁得仁又何怨”语见《论语·述而》。 (26)刘百昭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27)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