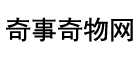请求详细介绍一下这四个人物?
章伯钧 (1895—1969) 安徽桐城人。武昌高等师范毕业。1922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1923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伐时任国
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第九军党代表。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底脱党。1930年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失败后流亡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一、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访问延安。1941年参与组织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和民主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47年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1948年,与沈钧儒等去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从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三届常委,第二届副主席,第四届委员。1969年病逝。
章士钊(1881-1973),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湖南省善化(今长沙)人,字行严,号青桐(青年时期)、秋桐(中年以后),晚年笔名孤桐。清末秀才。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次年便成为学潮的领头人,到上海投入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爱国学社。同年5月任任上海《苏报》主笔,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同时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协同黄兴筹建"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爱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民立报》主笔,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京国民党政府南北议和代表,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曾主编《甲寅》周刊。1927年为营救李大钊奔走。1933年起在上海作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总理向他介绍章士钊先生,尊称其为"我们的大学问家"。晚年曾为沟通海峡两岸出力。著有《柳文指要》等传世。
章炳麟,即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年) 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鲁迅先生曾十分推崇他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并誉之为“后生的楷范”,(参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辛亥革命后,他退居书斋,钻研学问,粹然成为一代儒宗。在学术上,他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一生著述颇丰,文字较古奥难懂。主要著作由后人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网罗繁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
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什么东西啊
政治设计院是反右时按给章的罪名。那段时间他经常和一些知识分子民主人士聚会,于是有人诬陷他搞反 联盟。比较典型的时章罗联盟。
章伯钧时至今未被平凡的五个右派之一。
改革开放后明确五个大右派不得平凡,章是右派之首
57年的反右派,官方的观点是没有错,错的只是反右倾扩大化了。如果全部平凡了,那就承认反右派错了
其实章伯钧确实在建国初够右的。他历史也不干净。22年入党,参见南昌起义,27年11月在党最困难的时候他退党了
徐悲鸿姑姑是谁的妈妈
孙姑姑1912年出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孙传瑗先生,字养癯,饱读诗书,又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一度风光,做了安徽省政府的委员,还做过孙传芳的幕僚。自孙大帅倒台后,受到牵连,获罪入狱。此后,失意闲住,以诗赋消磨时光。母亲汤毅英,出身名门,能文善画,曾任安徽第三师范学校校长。三位结义姐妹都是她的学生,她后来参透世事,吃素念佛,远离红尘,不问俗事。
孙姑姑,自幼十分聪慧、文静,受父母宠爱,但家庭对她的教育十分严格,父母亲授诗书经籍。孙姑姑最爱诗词,《红楼梦》中的诗词皆能背诵。养癯先生期盼爱女日后成为一位博学的才女。但孙姑姑自幼也爱上绘画,起初喜欢描摹线装书的绣像,渐渐不满起来,更喜对景写生。养癯先生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这丫头在这方面还有点儿天分!”
孙姑姑很快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1929年,奉父命去南京投考中央大学中文系,不幸落第。她便有意攻读自己酷爱的美术专业,要求先在中央大学美术系旁听进修,待来年再正式投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养癯先生无奈,只好答允女儿的选择。
初遇悲鸿互生慕
1930年,孙多慈进入中大美术系旁听。当时,徐悲鸿先生是中大美术系的教授、主任。徐悲鸿一向爱护青年,重视人才。孙多慈天生丽质、端庄淑雅,她的聪慧和绘画天赋,很快引起徐先生的注意。加上这段时间,她父亲因受孙传芳的牵连,正在南京坐牢,家境窘迫,孙多慈不免常顾影自怜,更使徐先生对其产生爱怜之情。孙多慈进入中大后得蒙徐悲鸿的亲授,还将自己的素描让孙多慈带回临摹,另外还特地给她开“小灶”,殷勤指导、启发、诱导,使她的学业飞快进步。后来徐悲鸿还为这位女弟子画了一幅肖像,题曰:“慈生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爱惜与期待之情溢于言表。而孙多慈自遇徐师以后,也深怀感激、仰慕、庆幸之情。由此可见,徐、孙相遇之初,互相产生好感是自然之事,至于婚恋之意恐怕当初是没有的。一个单纯而又受礼教影响的少女,是不敢妄想的;一个有妇之夫的尊严师长,也是不敢妄想的。
1930年夏秋之交,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中大美术系,本想在艺术的殿堂中进一步施展其才华,不料中大校园和美术界忽然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攻击所谓“徐、孙师生之恋”,骂徐悲鸿好色,有失师道尊严;说孙多慈轻浮虚荣,破坏老师家庭。
对这件事的小题大做,笔者认为原因是复杂的:
第一,其时国难日益深重,徐悲鸿对持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深感不满,公开批评,并参加田汉等人的南国社的进步活动。多次拒绝张道藩请他为蒋介石作像的要求。在广东、广西两省将领发动反蒋的“六一”运动后,又义无反顾地跑到桂林去。这些必遭国民党上层的忌恨。有人借机拿他的私事炒作就不足为奇了。第二,在艺术上徐悲鸿是坚定的写实派,尖锐地抨击过抽象派、野兽派等现代流派,与不同流派的同行颇多争吵,难免有人乘机攻讦。第三,最重要的是徐妻蒋碧薇醋意大发,直接干预。孙多慈以第一名考入中大美术系,国画为满分一百分。蒋获知此事,逼迫徐悲鸿出国。徐迫于内外压力,向中大递了辞呈离去(后因故未能成行)。1930年2月,徐在寂寞无奈中作《台城夜月》图,画中俩人同在一山冈上,徐席地而坐,孙侍立一旁,颈间纱巾随风飘动,天空一轮明月。徐的这副得意之作,可惜被蒋碧薇攫回毁灭。
徐、蒋当初私奔巴黎,原是艺坛一段佳话,不过后来环境变迁,志趣各异,逐渐在感情上出现裂痕。加上蒋背后有个倾心于她、身居高位的张道藩,这对徐悲鸿感情的打击是致命的,伤及肺腑。徐悲鸿心中的痛苦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日后母亲经常长叹一声,评价徐、孙之恋:“唉,你孙姑姑和徐先生的事,三分是师生情,七分是他们逼出来的!”此言不谬!社会和蒋碧薇意在逼迫徐、孙拉开距离,而事与愿违,世事却把孙多慈一步一步地推向徐悲鸿。
红豆戒指“慈悲缘”
确实,徐悲鸿已渐渐爱上孙多慈了!
当徐的好友舒新城来访,见到《台城夜月》后,联系外界所闻,询问徐的真情。徐坦言自己已爱上这位女学生。不久,徐在致舒的一封函中详述了恋孙之苦,并附诗: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胜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虽然徐悲鸿很少来校,但多慈姑姑仍不断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同学的无端攻击和骚扰,在教室的黑板上时有侮辱徐、孙的字句。为了避嫌,孙多慈也很久没有到徐悲鸿的画室中去了,但是孙多慈对恩师的爱意却也从灵魂的深处爆发出来了!
一天,孙多慈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与力量,竟然不顾一切,昂首走进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的画室。她看到站在画桌前的徐先生,脸色苍白,双眉紧锁,在宣纸上专心作画:几根老枝,几片枯叶在风中挣扎,几只麻雀逆风飞行……徐先生猛然发现了面前的孙多慈,不由得一阵心痛,微动着嘴唇说:“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此时,孙多慈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猛地扑在徐先生的怀里,号啕大哭,眼泪肆无忌惮地汹涌而出,把徐先生灰布长衫的前襟湿了一大片。徐先生也百感交集,却凝然无语,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长发。
这一天,可能是他们从师生情发展到师生恋的明白宣告!
1934年,孙多慈在中大美术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原先徐悲鸿已与有关方面疏通好,利用比利时政府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资金,让她去法国深造,不料此事也被蒋碧薇搅黄了。出于无奈,孙多慈只好回到安徽,在省立安庆中学任教,内心非常痛苦。立志一生从事美术教育,课余致力作画。这年冬天,徐悲鸿作《燕燕于飞》赠孙。画面为一古装女子,愁容满面,仰望高飞的燕子,上题:“乙亥冬,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传递了对孙的思慕之情。
1934年4月,孙多慈致信徐悲鸿,流露了对恩师的感激和爱慕之情,也倾诉了胸中的苦闷,表示要十年不通信,专心求艺,以期实现恩师的厚望。徐深为感动,回信勉励她继续努力作画,并将私蓄五千元钱托舒新城以间接的名义向孙购画,盖因他知道孙家经济拮据。
一个月后,徐突然来安庆,由孙多慈和李家应陪同,盘桓二日。这是徐临去桂林前来向孙告别。徐悲鸿远走之后,孙多慈给他寄去一粒她在天目山野外写生时采来的红豆。虽然孙未着一字,但王维《红豆》诗的寓意是尽人皆知的。
徐悲鸿接到红豆,恋情难抑,作红豆诗三首寄孙。
其一为:灿烂朝霞血染红,付与灵犀一点通。千言万语从何说,关山间隔此心同。
其二为: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其三为:急风狂雨避不恭,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心中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徐悲鸿还打了一枚戒指戴在手上。把红豆嵌在上面。背后镌刻“慈悲”二字。
徐、孙之恋,红豆作证,昭昭于天下矣!这时的徐、孙是很痛苦的,也是很幸福的!
乱世悲情多磨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母亲叶庭筠和孙多慈两家结伴而行,开始向内地流浪。流浪到长沙,形势稍稳定。我家和孙家住在桂花井街的一个大宅院内。
一天,母亲和孙多慈姑姑要一道出门去,孙姑姑穿了一件未见穿过的灰色法兰绒大衣;母亲也穿上从上海买来的从未穿过的狐皮领大衣。她们这种特别隆重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知道她们去会见徐悲鸿先生。
徐先生是去桂林的途中在长沙作短暂的转车停留。她们赶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客栈去会见徐先生。徐、孙两位恋人在战乱中偶然相见,自然十分快乐。徐先生见到初次见面却久已心怀感激的母亲;母亲见到她小妹心仪已久的知心人,也感到十分亲切。徐先生邀请她们到附近的一家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徐先生忽然问道:二位女士,你们可知道长沙人的筷子为啥做得这般长?她们端详着长筷子答不出来,正在这一瞬间,徐先生用那筷子夹了一块炒腰花,隔着桌子,径直塞到坐在对面的孙姑姑嘴里,笑着说:“长筷子的妙用在此也!”把两位女士都逗笑了。
饭后回到小客栈,孙姑姑代母亲向徐先生求画,徐沉吟片刻后从皮箱里取出一幅《立马》相赠。原题有字样:“秋风万里频回首,认识当年旧战场。悲鸿写于桂林,廿六年八月与倭寇鏖战之际。”当即挥毫补题:“庭筠女士文豪惠存。廿七年四月七日台儿庄大捷歼敌两万人,志之于此,永为纪念。”
母亲珍藏此画数十年,是她辞世后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
这次长沙相晤,孙姑姑邀大姐即母亲同去,是为了商量她和徐的婚姻大计。徐、孙从师生情发展到师生恋,经历了风风雨雨,重重折磨,他们内心都十分矛盾、痛苦,都想在这次见面时,把问题摊开、说透,并让母亲当“参谋”。
他们谈到什么程度,母亲当然不会同孩子细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孙姑姑对徐先生的感情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特别是母亲与徐悲鸿接触后,对徐本人和他与孙姑姑之间的深爱,有了进一步理解,成了他们婚事的积极支持者。他们下决心了。只是因为徐先生急着要赶回桂林,他们的婚事要等孙到桂林才能作安排。
以后在长沙的几个月中,孙姑姑似乎已经摆脱那种忧伤压抑的心境,开朗愉悦起来。那时,我们两家常一起到附近的长沙名胜天心阁去玩。孙姑姑穿一条黑色长裤,白衬衣,领口是一个黑蝴蝶结,微风徐徐拂动她的柔发和胸前的飘带,衬托着她端庄、娴静的神态,真是美丽。
到了暑假,局势又紧张起来,我们一家逃到湘江对岸的农村去躲避轰炸。孙姑姑忽然来信,要母亲陪她们孙家一同去桂林。母亲狠心地把我们几个孩子托给并不很熟的房东,匆匆过江而去。
在桂林,徐悲鸿与孙多慈多次见面,他们在一起度过许多快乐的日子,他们一同观览了桂林和阳朔的山水,一起作画。母亲是见证人。我家现在还存有徐悲鸿的一幅《鹩哥》图。徐在上面题词:“丁丑大暑,为慈作画”,落款是“阳朔天民”。画上的两只鹩哥,神态极为生动,像是它们互相在倾诉绵绵不尽的情话。这正是他俩在桂林这一短暂而快乐相处的写照。
孙多慈有什么情况,总是和母亲商量的。但最终她和徐悲鸿的感情却没有结果。母亲没有和我说过详因,但我推想,也许是因为:
第一是蒋碧薇不甘心。徐悲鸿和蒋碧薇当年私奔,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生儿育女,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婚姻。现在要脱离这种同居关系,徐悲鸿曾请教过章伯钧等法律专家,以为从法律上看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他俩早已破裂,而蒋出于报复心理,大造舆论,造成对徐悲鸿不利的社会和家庭压力。蒋声称,决不让他如愿以偿,在经济等方面也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更索要徐的一百幅佳作和珍藏品。徐悲鸿忍痛满足了这些要求,但并未取得蒋碧薇的谅解和允诺。
第二是孙姑姑的父亲孙养癯的坚决反对。孙父是一位道学家,也是一位看重仕宦的人。他有一子一女,儿子不成器,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全寄托在女儿身上。他心中的乘龙快婿应该是一位高官,他看不起画家,更反对与有妇之夫的老师发生婚姻关系。虽然徐悲鸿的画名很高,为人敬重。但他对徐仍是不屑。蒋碧薇的回忆录中提到,在这期间,“徐先生曾托人到孙家门上求婚,被孙老先生大骂一顿,悻悻地出国去了”。
师生苦恋终飘零
杭州沦陷后,浙南的丽水成为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
母亲和李家应姑姑经过约一个月的颠沛之苦,来到丽水碧湖镇。李家应时任浙江第一保育院院长,母亲应聘在保育院工作。稍后到达的孙多慈在碧湖的浙江省联合中学任教。
孙姑姑除任教外,也有画不完的题材,有时还邀请潘天寿、郑仁山等画家一起到李家应院长的会客室里作画,她泼墨挥毫,高谈阔论,显得格外高兴。
然而孙姑姑尽管脸上有了一抹明媚的阳光,但心底的乌云却是挥之不去的。
徐、孙的婚事虽遭挫折,但是两人的感情依然浓烈。徐在海外,虽云天万里,战火纷飞,鱼雁阻滞,但是他们还是通了不少信,其中许多中途失落,收到的是少数。
1939年9月,徐往印度讲学,10月携作品到香港展览,收到孙多慈一信。
徐回信劝她不要消沉。随后孙又发一电报,要徐到浙江去。可是徐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岂能更动。
徐于12月抵印度,邮路阻隔。两人音信从此中断。他们的婚事更是渺茫。
但是此时的孙多慈已快三十岁了,这位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教师,在浙南山区当然是令人十分注目的,也不乏崇拜和追求者,其中包括一些达官显要。
一天夜晚,三姐妹正在房中谈心,忽然闯进来四个提着红灯笼的卫兵,递上名片,说“××将军敬请小姐面谈”。
来者不善!
母亲说:“今夜已晚,可否明天上午让孙小姐去拜访将军?”不许。母亲要求陪同前往,又不许。无奈,孙姑姑进里屋换衣服。母亲嘱咐她:“看来今天不去是不行的,去就去,不要怕!他是中央要员,估计还不至于胡来。他如果有什么无理要求,你厉害些,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深夜,孙姑姑才由四个卫兵护送回来。她面色苍白,等卫兵一走,就忍不住抽泣起来。
原来这位将军到碧湖来,并无军情要事,是专程来向孙求婚的。她当然严词拒绝了。
奇怪的是,这位将军对她的事了如指掌,什么“徐先生在海外音信渺无,生死未卜”;什么“你家现下经济拮据,老太爷的脾气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怎能发挥你的艺术才能”,等等。这些话虽然没有说服她去当这位将军的抗战夫人,但使她的精神防线发生动摇。
除了徐悲鸿的杳无音信,家庭经济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父亲孙老先生长期赋闲,老太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母亲除料理一些家务外,主要是念经拜佛。一个哥哥长得相貌堂堂却终日无所事事。吃的用的,全部负担都压在她纤弱的肩上。战时物价飞涨,教师工资微薄,真使她心劳力绌,烦恼异常。是啊!是应该找个合适的人嫁了!
许绍棣就这样凸现在她面前了。
许绍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权重势大。他外貌儒雅,热心抗战事业,为办战时流亡学校作出过一定成绩,生活也尚简朴,政界的名声尚佳。他于抗战前夕,中年丧偶,有两个女儿,名绛烟和黛烟。他体弱多病,早想续弦,已追求孙多慈多时。但文化界也都记住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人”“提出呈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禁止鲁迅著作在浙江出售,此人便是早年的许绍棣。故其在进步文坛中声名狼藉。加上他与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绯闻流传颇广。因此,开始时叶、李两位义姐是持反对意见的。
中国第一任交通部长谁?
开国部长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等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章伯钧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同国民党作斗争。1月16日,他就共同纲领问题发表意见。17日,他重申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国民大会的五项主张。会场内外,章伯钧十分活跃,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挥他的口才和文才,痛快淋漓地斥责国民党当局,热情洋溢地赞誉共产党。他对国民党的政要说,莫要崇拜单纯的武力,轻视人民,最安全的道路,是走政治的途径。
当蒋介石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强行召开国民大会时,中共代表团拒绝参加。章伯钧等民盟代表也拒绝出席。他还和其他两人一起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民盟维护政协决议;二、民盟反对内战。这对中国共产党是极大的支持。1947年2月3日,章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认为抗战胜利后,已转入国内民主革命,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担负新的历史使命,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章伯钧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
杨宝忠的人物评价
夕阳十里,西风一叶。一个极具才情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是很弱、很弱的。杨宝忠广结人缘,最后却是孤立无援。杨宝忠生性乐观,而离世的那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眼中可有泪?他的死,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谋”的结果。我敢断言:那些发现他在北京西单乐器行坐着的人,一定是年轻人;那些把他押回天津并关进无取暖设备小屋的人,一定是年轻人;还有那个掌管着小屋钥匙却不给他送饭送水的人,一定也是年轻人——他们一定就是天津戏曲学校的学生、造反派。不错,“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可杨宝忠却是直接被这些人弄死的。这不是“合谋”是什么?“文革”的血腥战果,正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名曰“革命群众”的个人来实现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痕,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在领袖号召下,在革命组织的策划主持下,由熟人、亲人、同事、部下、朋友、学生、街坊、邻里直接动手干的。我们自己“应该反省,手上是否有血痕?”——前不久,女作家方方说的这句话,指向的是一个并未消失的现实。害死杨宝忠的年轻人,大多数现在可能都活得很风光,也心安理得。章伯钧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感兴趣,这可能与他德国留学时住在犹太人家庭的生活经历相关。父亲曾明确说:迫害犹太人的暴行,纳粹希特勒是罪魁祸首,但也有全德国民众的狂热参与。这就是说,数百万犹太人被关押、被屠杀的罪行,也是上与下的“合谋”了。如今有成就的京剧琴师,可以独自举办专场音乐会,甚至是京剧胡琴交响乐音乐会。以京剧曲牌“夜深沉”命名的大型乐曲,也已搬进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掌声、鲜花、欢呼、赞美、恭维,艺人终生期待的东西,应有尽有。遗憾的是,杨宝忠没赶上这些专为中国京剧音乐弓弦大师举办的盛典。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些盛会都属于古典与流行时尚的“对接”,中国传统艺术落到了这个份儿上才风光,说明它自身已虚弱到快要咽气了。所以,杨宝忠也不遗憾——他活在中国京剧真正繁荣的鼎盛期。真的,文化方面的事物很难判断它的正与反、先进与落后、幸与不幸。“故人何在,前程哪里,心事谁同?”杨宝忠的灵魂是慢慢地从躯体中离去,恍似白云一缕,袅袅舒卷于天际。我们若隐隐听到从远处传来“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咏叹,请勿惊惶,那是杨氏昆仲在另一个世界又继续他们的粉墨生涯了。
章伯钧的政治失败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反革命”——而实际上,“右派”就是反革命。